
僅為情境配圖。取自pexels
過度簡化因果的謬誤可能以無數種風格呈現,最常見的莫過於「假二分法」(false dichotomies)或「假兩難」(false dilemmas)。這都是在兩個極端選項中進行選擇,即便兩者之間其實還存有無限種其他選項。然而,儘管假二分法本質上很空洞,但卻超級適合用來妖言惑眾,將大量可能性縮窄為只有大約兩個選擇。如果這種過度簡化的修辭花招被觀眾接受,那麼演說者就能馬上提出一個二選一的結果,一方是「讓人滿意的」,另一方是「卑劣的」。也因此,假二分法天生就是偏極化和不妥協的。這種謬誤的權謀特質在於:它能用來迫使無黨派的人或未結盟的人,要嘛與說話者結盟,要嘛就是丟臉。它帶有一個暗示:不完全贊同說話者提議的人,會被暗示(有時則是明示)為敵人。(本文摘自《反智》一書,以下為摘文。)
這些都是胡說八道,卻有力得驚人,具有磁鐵般的能力,可以讓不夠警覺的人按照說話者的意願來站隊。可想而知,它在政治發展史上由來已久,最顯著的形式就是:在橫跨政治光譜的所有譜線中,宣稱「你要是不和我們一道,就是與我們為敵」。
列寧在1920年的一場演說中宣布:「我們以絕對的坦誠來說這場勞工階級的奮鬥;每一個人都必須在加入我們或加入對方之間,做出選擇。任何人想要避免在這個議題上選邊站,最終都將慘敗收場。」80年後,政治立場上與列寧天差地遠的美國總統小布希,在911攻擊後的國會聯席會議上演說時,也用了同樣這套開場白,警告所有正在聆聽的國家,「你要不站在我這邊,就是和恐怖份子站在一邊。」列寧和小布希兩人都毫無顧忌的採用赤裸裸的修辭謊言,來箝制一切聲音,只留下對自己有利的偏激觀點。
假兩難的漫長卑鄙的血統,同樣令人難忘。我們這本書的其他章節和市面上的許多書籍,都找得到歷史範例。
例如,米勒(Arthur Miller)的劇作《薩勒姆的女巫》,背景設定在1690年代麻薩諸塞灣薩勒姆鎮的審巫案期間,但寫作的時間是在1953年,該劇非常精采的諷喻了當時瀰漫整個美國社會的反共產主義的歇斯底里。劇中,副審判長丹佛斯便援引了這個謬誤,警告說「任何人只能與這個法庭站在一起,不然就必須反對它,沒有中間的路。」除了政治領域,假兩難也常用在情感性的話題,以推動特定的敘事,而其邏輯通常不健全,因為在光譜兩個極端的中間,其實還存有其他的合理立場。
假二分法由於自身的特質,天生就和理性論述相對立,容易孵化出極端主義。而假兩難天生的極端,可毒害到務實的解決方案,並擊碎建設性的對話。假兩難最深沉的魅力在於:它有辦法將整個光譜壓縮成簡單、互相對立的兩個極端,而這也解釋了,為何長久以來它會深受暴君與煽動家的喜愛。而且很明顯的是,假兩難的腐蝕性影響力並未隨時間減低,現在依然常出現在很多領域中,充滿了乏味的可預測性。這種現象在社交媒體裡就非常普遍——在社交媒體裡,具有極寬廣的細微差異觀點的複雜話題,往往被提煉成完全對立的二種詮釋之間的爭吵比賽。在這類論壇上,意見光譜變成了很奇怪的雙峰譜。

過度簡化謬誤的吸引力在於它很容易領會:它們提供簡單的、讓人寬心的解釋,來詮釋複雜的現象。這種「自己已經理解了」的錯覺,很令人安慰,也很令人肯定,是心理上的慰藉,也是在這個令人迷惑的世界裡的保護圖騰。
對人類來說,瞭解因與果的渴望十分重要,而且是天生的。這項持久的欲望,數千年來一直是驅動人類發展與追求知識的引擎。
它引領我們通往一切,從學會取火,到得出量子力學公式。若沒有這種無法壓制的理解欲望,我們今天將不會擁有如此大量的藝術與科學。然而,至少在我們還有欲望去瞭解的時候,一旦稍有不慎,我們也會淪為「因果謬誤」(causal fallacy)的受害者—因果謬誤早就書寫在我們的迷信裡,融入我們的儀式甚至宗教裡。
想要區分因和果,有可能非常困難,而且太容易出錯,太容易造成群體的傷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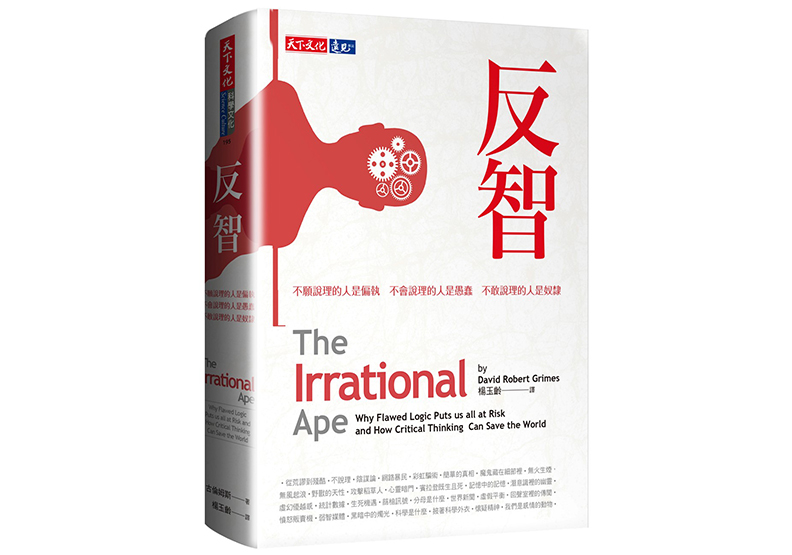
September 01, 2020 at 04:33PM
https://ift.tt/31P1uV8
政客最愛「假二分法」:你要是不和我們一道,就是與我們為敵! - 遠見雜誌
https://ift.tt/2N87ShW
Bagikan Berita Ini















0 Response to "政客最愛「假二分法」:你要是不和我們一道,就是與我們為敵! - 遠見雜誌"
Post a Comment